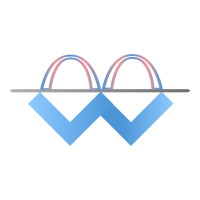(一)
阿花是一条身上有4种颜色的狗,按理说这种多颜色的狗并不多见,但是奈何他出生在穷乡僻壤里,他身上的花纹也就只有乡里乡亲见了会夸赞两句,说:唉呀妈呀,这狗娃子真俊啊。阿花是孤独的,他的父母都是长鼻子小眼睛的中华田园犬,他也无可奈何的继承了他们的特点。话说回来,即便是自己有4种颜色,在千万狗同胞里肯定也不会单有自己一个,更何况自己是条血统廉价的狗呢,所以当阿花和同村其他狗一起从泥潭里打滚之后,就不再想起自己有着和别人一样的四色毛色了。
日子一天天过,村子里的狗和人一样,过着小富即安的日子,既然不是牧羊犬,也不用难过主人家里穷到没有一只羊,既然不是雪橇犬,也不用抱怨这黄土高原上很少有能积住的雪,我只是一条土狗,我生下来就是和这片黄土为伴的。阿花常这么想,但阿花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爱上一只贵宾犬。
农村里是不会有人养贵宾的,那么阿花爱上的这只贵宾是哪里的呢?这要感谢国家的电器下乡工程了,一台电视机摆在了主人家原来放土地爷的供台上,阿花也凑热闹的跟着主人看起了电视,碰巧电视上正在演狗狗知识普及节目,一只贵宾就站在那个黑色的柜子里,阿花呆呆的看着贵宾,鼻子呼哧呼哧的响着。但当他缓过神想去找贵宾在哪时,主人已经把台调到了最爱的乡村爱情,随之而来的是刘能和赵四斗嘴的声音。
阿花恋爱了,他爱上了一台电视机,至少主人是这样认为的,因为他每天对着电视机周围转悠,主人只要稍一不留神,动物原始的冲动就会促使阿花做出羞羞的事情。但再怎么心急,那也只是台电视机啊,几天下来,阿花似乎明白了电视机的构造和同类的构造不太一样了。在明白之后,阿花就不再出去和外面的土狗厮混了,原因无他,没有一只狗会喜欢整天灰头土脸的狗。阿花开始在镜子里靠自己的样貌了,和小时候一样,除了背上四色的毛发,他和其他狗没有什么区别,相反,偷狗贼反而会因为他的毛发更容易套住他,对,更容易套住这只不想留在这里的狗。
阿花被套去了牲畜集散市场,他在一家狗肉店的笼子里待了三天。直到第三天凌晨,从居民楼上掉下来的花盆把笼子砸出一个足以供他钻出来的洞时,他才得以好好看看这不同于之前村子的地方,一只狗不会觉得霓虹璀璨是种奢糜,他们的世界大多也只是黑白的。阿花一个人走在冷风中,心里想着的是那只贵宾,但又有一些时候想着的是村子里那户人家,偶尔脑子里还蹦出那条和他在泥潭里打滚的狗的影子。
走着走着,脑子里的狗的样子都重合在了一起,他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,他临死前才意识到。自己从生下来就只有一种颜色,只是他有了精神分裂,和他滚泥潭的是自己,电视上的贵宾其实也是自己,那四种颜色只是四个不同精神状态下自己的颜色,他看着霓虹下的城市,狗肉店本想明天做掉他而给他打的毒针起作用了,他在生命的最后知道了自己探索的都是空的,却又在生命的最后才认识了自己。目光越来越黯淡,突然耳边传来一句话:阿美,快回来,那是条死狗,小心他咬你,他顺着声音看去,一个女人拽着她的狗,不让她的狗跑向阿花,而阿花,最终也没有看清向自己跑来的那只贵宾。也许,不该让它来打搅阿花本来就已经破碎不堪的梦了。
(二)
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农场,农场主是一个胖胖的老头,从他生下来以后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农场里度过的。他18岁那年双亲离世,留下苦心经营的农场给他。他起初是想卖了农场去城里好好打拼一番,但是等他找到农场的地契时,发现放地契的那个箱子的箱底被老鼠啃了个洞,地契也难幸免于难。他惶恐地过了好几天,生怕别人发现自己已经没了这个农场的地契了,可是过了几天,只到地里的庄稼都快黄了,他才发现根本没有人在意他的地契是否被啃了,内心庆幸的同时,对于农场里的老鼠毁掉自己计划好的未来这事耿耿于怀,连着三天,他拿着手电躲在仓库的角落里想制裁那只啃掉他未来的老鼠,可是愤怒他忘了老鼠不喜欢有光的地方,最后只好无功而返。躺在床上,半睡半醒的状况下仿佛还能听见老鼠啃东西的声音,内心难以抑制的火苗侵蚀着他的内心。第二天一大早,他就去宠物店买了只猫,并嘱咐店家务必要给他挑一只捉鼠能手。
带着自己的黑猫警长,他回到了农场。然而黑猫警长的死敌一只耳却没有应邀出席对警长的欢迎会,他把警长放在有地契箱子的那间屋子里,幻想着明天能在警长的嘴边找到半截没有吞下去的老鼠尾巴,然而一切和他想象的并不太一样。
当天晚上警长工作得并不顺利,警长在新的环境里竟然水土不服拉肚子了,然而作为一只高贵的警长猫,他要不能允许自己在猫砂以外的地方进行羞羞的事情。总之在警长万般无奈的情况下,一只耳出现了,在箱子后面的洞里探出一个鼠头,警长的本能和一只耳的本能分别告诉各自,对方不是好货色,但是一只耳看着捂着肚子的警长似乎知道他遇到了什么困难,无奈一只耳心善,从箱子里叼出来半拉地契,终于解决了警长的困难。等警长解决完之后舒服的趴在地上,一只耳又出现了,碍于刚刚帮助了自己,警长并没有对一只耳做出什么,一只耳在警长旁边也躺下了。月光从破旧的仓库墙缝隙中打下来,警长从怀里拿出一包大前门,递给一只耳一只,一只耳拿过来别在了耳朵上,看着警长,警长的背影洒在自己的面前,一只耳永远不会想到自己和一只猫会相距这么近,警长把头扭向一只耳,又摇了摇头看向了远方,幽幽的说了句:我说今晚月色那么美。 一只耳说:是的。
(三)
我是一件快递,当我被揽收在快递小哥的自行车后座上时,我的生命才刚刚开始。其实这可能不是我第一次当快递,但是我却记不得上次我是快递的时候我在哪里。快递小哥从一个胖男人手中将我拿走,再三确认后在我的脸上贴上了属于我的标签:寄件人 张某某 收件人 废坑。对,我的名字无外乎在这两个名字之间罢了,哦对了,或许还有一串数字能证明我的存在,但我觉得那些单单只是排列着的数字远没有这些方块字讨人喜欢。
我在凌晨时分上了一辆开往城外的货车,同行的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快递,我和他们一样,都保持着沉默。并不是我生来就不喜欢说话,只是我们都知道,舱门一开,就会有一批同伴要与我们分离,我们每个快递都不愿意见到朋友的分离,哪怕只是三言两语的朋友也会让我们感到痛苦,既然如此,墨守成规的便是沉默,命运安排我们的也是沉默。黑暗中的沉默让我有时间重新认识自己,我把我身上的标签一遍又一遍的读着,这于我来说像人类身体里的染色体一样,从一开始就不由自己决定,却要由它来决定之后的我。
车还在不停的前进着,我身旁的快递大多数都已经不见了。只留下我和剩下两个,我凑近了看,才发现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一样的,都是废坑。即便如此,我还是没有拿出和他们交谈的勇气,我不知道从车厢出去以后的世界,却也拒绝了解车厢之内的世界。车停了下来,不出意外,司机打开车厢把我们三个快递一同取了下来。时隔多日,我又见到了阳光,虽然我并不依赖着阳光而活,但是死板黑暗总归让人厌恶。就在司机转身去关上车门的空挡,我有机会看到了我要去的地方——废坑。
我确乎是看到了一个坑,一个深不见底的坑。坑周围停满了从四面八方来的快递车,时不时有几件快递从坑边落下去。到了现在,我明白了坑前面的废字了。开了几天的车,司机似乎也颇为疲倦,他无力的抱起我们三个快递,走向坑边,松开手,我们坠落……其实,我并不生气我的结局是这样,不是因为有成百上千的快递和我一样所以我才不生气。也不是因为快递公司提前就在快递单上写了“新服务:隐私物件报废处理” 而提起知道我的命运才不生气。我只是从一开始就知道命运并非由我掌握,而我,走过命运所安排的世界,看过种种看似蹊跷,荒唐,光怪陆离的社会和同我们一样卑微的人类,才无惧于命运最终对我的宣判,但最终我还是违背了命运,对我身旁的那件陪着我在车里度过几天几夜的快递同伴说了句:“嗨!”